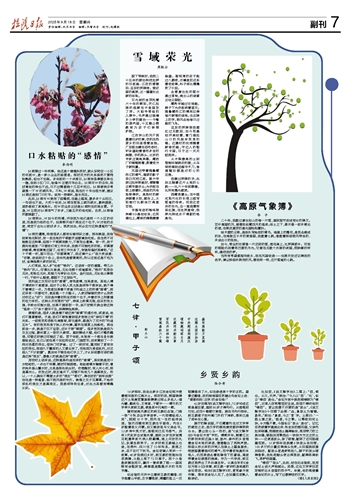
《高原气象簿》
李 平
二十年,我数过唐古拉山的每一片雪,直到指节冻成苍白的碑文。百叶箱里的风,曾替我收藏四月的温柔;冻土之下,春天像一封未寄出的信,在铁皮屋顶的星光里轻轻颤抖。
纳木措的云图,是连队写给我的情书。准星上的霜花,是思念凝成的冰,在海拔五千米的黄昏里,我数着心跳,像数着那些被风带走的、未说出口的告别。
如今,转业的印章像一片迟到的雪,落在肩上,比界碑更冷。可我的眼睑仍刻着岗巴营的月光,它曾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,把缺氧的呼吸,缝进我的梦。
当所有希望都指向故乡,我在风里低语——如果天空还记得我的名字,请让那些未测完的风,替我吻一吻,这片雪域的心跳。




 藏公网安备 54010202000024号 | 地址:西藏拉萨市江苏路19号 | CopyRight :拉萨日报社
藏公网安备 54010202000024号 | 地址:西藏拉萨市江苏路19号 | CopyRight :拉萨日报社